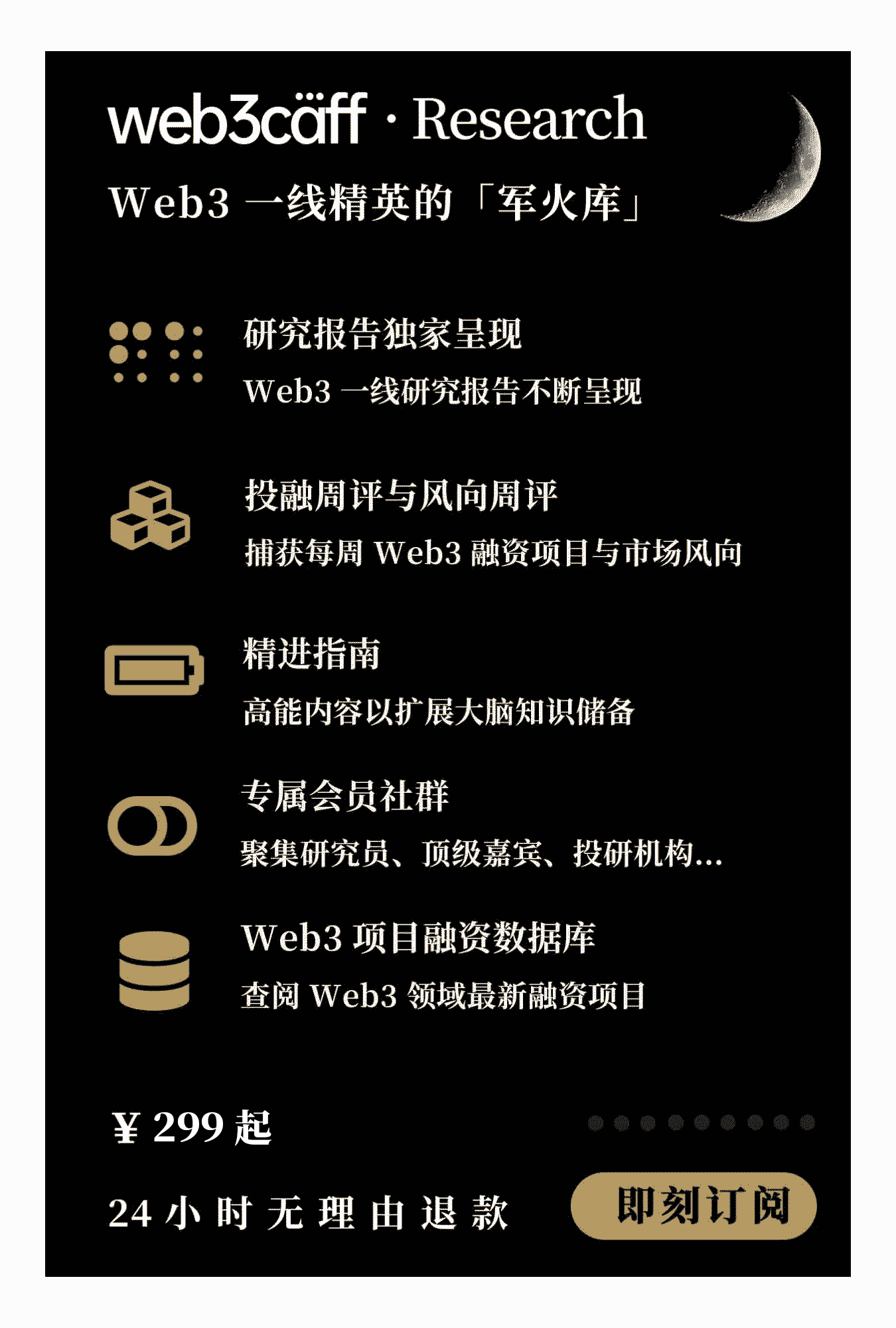關於 VC、媒體和科技行業關係的討論。
原文:The Unauthorized Story of Andreessen Horowitz(Newcomer)
從親近媒體到選擇直接發聲,Andreessen Horowitz(a16z)的轉變只是科技產業與媒體產業關係惡化的一個縮影。這篇文章講述了諸多 a16z 未曾公開披露的故事,關於 VC、媒體和科技行業關係的討論,作者為前彭博社記者 Eric Newcomer。

曾在 a16z 擔任內部分析師的 Benedict Evans 多年來一直在想,“ a16z 是一家通過 VC 獲利的媒體公司”。
這個看法變得越來越真實。
雖然 Twitter 上一直流傳著許多拋棄媒體選擇 “直接發布” 的非正式言論,但 a16z 是真正有意識、分步驟地採用了這種做法,該公司的戰略對媒體和風險投資行業的未來有著巨大的影響。
這是一篇關於 a16z 如何通過先向媒體示好,隨後又故意拋棄了與媒體的良好關係,進而擾亂風投世界的報導。
我們現在從頭講起。
大約在十年前,Margit Wennmachers 給記者 Kara Swisher 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Kara Swisher 在騎馬運動的休息時間裡寫了一篇報導,提到 Margit Wennmachers 將離開她與 Caryn Marooney 共同創辦的傳播機構 Outcast,以正式合夥人的身份加入成立一年的風險投資公司 a16z ——矽谷裡很少有女性能獲得正式合夥人的頭銜,在 2010 年的時候更是如此。
在接受 a16z 的內部播客採訪時,Wennmachers 解釋了她在早期的公司定位策略。她回憶道:“我想嘗試登上一個封面報導,因為——現在它聽起來很老套,人人都在 Twitter 上讀新聞,都在看網上的東西——但是封面報導仍然具有一種聲明的作用,它是那種你在機場裡能看到的宣傳物料印刷品。 ”
藉著 Wennmachers 在媒體方面的特長、Marc Andreessen 的 “一秒鐘的想法” 模式以及 Ben Horowitz 的威望,三人在矽谷掀起了一場風暴。這家公司為搶手的公司出價,為創始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務,並不遺餘力地向媒體宣傳著自己的故事。
在 Wennmachers 的鼓勵下,Andreessen 於 2011 年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專欄文章,題為《為什麼軟件正在吞噬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這句話現在已傳的人盡皆知,以至於各種各樣的宣傳都會高喊著 “xxx 吞噬世界”。
“ Margit Wennmachers 確實是這家公司的隱藏創始人,Marc、Ben、Margit 三人掌握了公司的權力機制”,一位曾從該公司籌集資金的創業公司創始人告訴記者。
通信主管和記者們都敬畏於 Wennmachers 對媒體的影響力。一位公共關係人士表示:“矽谷里內部消息是:她是最好的人選,非常出色。我永遠不會想和她交惡。”
雖然 Wennmachers 在早期階段的策略對於許多好萊塢和華盛頓的人士來說是非常熟悉的,但她在當時俱樂部式的、高大上的矽谷裡卻顯得不太常見。“她會說她的工作是管理信息,以便於塑造敘事”,一位了解 Wennmachers 的知情人士表示。
Wennmachers 利用行業八卦和她與公司合夥人的接觸來保持其在眾多記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
一位在 a16z 投資的公司的通訊主管回憶道,Wennmachers 曾為記者打探過一個即將發布的消息,這位高管稱 Wennmachers 親自將打探到的信息傳遞給了記者。
一名公關主管(來自存在競爭關係的某家強勢企業)則將 Wennmachers 描述為一個強勢的人。“你不能越過我們(發布消息),如果你越過我們,我們就會掐斷信息的流通。”
一位新聞界人士回憶說,Wennmachers 追查過一條潛在的新聞。當她回電話給故事潑冷水時,記者從容應對。Wennmachers 告訴記者,他們現在是 “好朋友” 了, 這句話讓記者覺得很奇怪。他們只是想弄清事實。但 Wennmachers 的態度似乎反映了她對盡職盡責報導矽谷的記者所期望的一種舒適感。
Wennmachers 會定期在她位於舊金山普雷西迪奧附近的家中舉辦沙龍式晚宴,邀請記者、投資組合公司、公司的合夥人參加。
雖然風險投資公司宴請記者並不罕見,但 Wennmachers 做得比其他人要好。我在 2014 年受邀參加她的一次晚宴時,感覺自己終於被邀請到了矽谷的內部圈子。
“我受邀在她家與媒體成員共進晚餐。這真是不可思議,” 一位創始人回憶道,“那就像是一個很酷的邀請。如果你是媒體人士,那麼能在 Wennmachers 家吃飯真的是一件興奮的事情,想一想就有點讓人心動。”
Wennmachers 可以裝出一副友好的面孔,但和她相處的時間長了你就會意識到她是一個深刻嚴肅的人。她並不是因為有趣而贏得記者們的青睞,而是因為不講那些廢話。她能根本上理解什麼才是一篇好的報導,她比許多記者更加了解一個記者的動機。後來,a16z 轉變成與媒體對立的態度,部分原因就在這裡。
在早期的媒體全盛時期,Wennmachers 會把公司的合夥人分配給媒體公司。這些媒體公司都渴望合夥人在有利可圖的會議上發言,而公司的合夥人則是以大膽的措辭來預言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用自己的言論填滿記者們的專欄版面。
Swisher 和 Wennmachers 這兩位女性在一個男性占主導地位的行業中一路攀升,且至今仍然保持著友好的關係。許多矽谷內部人士強烈懷疑,Swisher 報導矽谷日常新聞時的一個消息來源就是 Wennmachers,但 Swisher 自稱 Wennmachers 對她自己的公司非常忠誠,儘管 Wennmachers“在我可能打電話詢問某個問題的時候,不會裝作不知道。”
Marc Andreessen 本人與 Swisher 這樣的記者保持著一種親密的關係。“Marc 自行處理所有的溝通,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已經不再想和媒體打交道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他犯過的一些錯誤。”
在 2009 年到 2015 年期間,a16z 贏得了一系列真正驚人的新聞報導,把自己推到了風險投資公司的最頂端——至少就聲譽而言是最頂端。媒體喜歡那個互聯網光頭極客(指 Marc Andreessen)還有他那位看上去五大三粗的大師級商業助手。記者們在巴特利酒店的雞尾酒會或午餐會上會向 Wennmachers 打探消息,即使報導中很少提及她。
然後,雜誌作家 Tad Friend 為《紐約客》推薦了一篇關於 Marc Andreessen 的簡介。Wennmachers 發現公司在大眾意識中的地位已開始轉變,它不再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新秀。
“在那個時候,我正處於一個階段,就像是說'夠了','我們已經談論自己談得足夠了。”Wennmachers 在播客採訪中表示。
另一方面,她認為 “《紐約客》就是《紐約客》,所以《紐約客》隔多久才會寫一篇關於風險投資的權威文章?十年一次嗎?也許吧?那麼,我該希望這篇文章是在寫別人,還是在寫我們?我想在報導裡佔一個位置嗎?”
她決定完成這個報導,儘管她自然不會佔一個位置,她只值得被順便提一下。Marc Andreessen 那顆閃閃發亮的腦袋反而成了焦點。
這篇報導於 2015 年 5 月刊登,題為《明日先鋒的前進者》(Tomorrow's Advance Man), 報導中那幅閃耀著光芒的畫像立即成為了關於風險投資行業的一篇開創性報導。
儘管文章篇幅長達 1 萬多字,但文中只是順便提到了 Zenefits。Zenefits 是 a16z 最重要的投資之一,曾大手筆地投資 Parker Conrad 的人力資源軟件公司,並在媒體上大肆宣傳。但是,裂痕已經開始出現。
2015 年底,Buzzfeed 記者 Will Alden 對該公司的健康保險經紀人是否獲得適當許可提出了質疑,此舉種下了令 Zenefits 解體的一顆種子。
同年,John Carreyrou 透露 Theranos 公司 “在血液測試技術方面遇到了困難”。Theranos 主要在矽谷以外的地方籌集資金,但一些風險投資家還是將他們的聲譽與維護該公司聯繫在一起。Marc Andreessen 當時在推特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當時有人選擇屏蔽了在推特上對 Theranos 持否定態度的人,而 Marc Andreessen 在這群人中似乎形成了一種親和力。
對記者來說,尤其是他們的編輯來說,Theranos 公司的故事表明科技記者需要對他們報導的初創企業持有更多的批評性眼光。Carreyrou 是一名根本不在矽谷工作的調查記者,而科技記者們不應該忽略 Theranos 公司的缺點。正因如此,他們就加倍努力了。
後來,a16z 確實發現自己的投資組合公司也有問題。2016 年 5 月,我在《商業周刊》上報導了 Zenefits 的 “自爆”,同時還有眾多科技記者也挖掘了該公司的失敗。
而在當時的幕後, Wennmachers 的最高副手 Kim Milosevich 將公司 “自爆” 的大部分責任指向其聯合創始人 Parker Conrad ——他當然應該為公司的問題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
但 a16z 的合夥人 Lars Dalgaard 曾為 Conrad 打氣,安慰 Conrad 已經將公司的收入增長目標提高一倍,我當時也報導了。Zenefits 是 a16z 想要發展、發展、再發展的公司。
幾年之前,Ben Horowitz 本人曾寫過一篇文章為 “肥胖的初創企業”(即那些積極花費以阻止其競爭對手的企業)辯護,Zenefits 似乎正在運行這套遊戲規則。
但隨著公司的業務開始動搖,監管風險在不斷增加,Horowitz 介入並推動 Conrad 讓位。該公司將責任歸咎於 Conrad,同時一直擔任公司首席運營官的 David Sacks 則被當作扭轉局面的首席執行官來向全世界推銷。
同年,媒體開始把注意力轉 a16z 本身,想知道它是否真的配得上多年來的炒作。
《華爾街日報》記者 Rolfe Winkler(我偶爾會和他一起打橋牌)在 2016 年 9 月的報導中寫道,a16z 的回報率落後於 Benchmark 和 Sequoia 等公司。
作為未來情況變化的一個早期跡象,a16z 發表了一份閒談式的公開回應。
這是記者們非常熟悉的一種反駁方式。公開場合下,當事人大喊報導全錯了,報導播出後,再發表了一篇沒有具體矛盾細節的博客文章。在內部,PR 團隊對事實核查中任何可信的東西都不反對,也不要求事後更正。
a16z 希望人們認為它做得很好,而不是很差。當然,這篇博客文章在 Twitter 上引來了一群狂熱的忠誠者,他們紛紛抨擊媒體。
a16z 的合夥人 Scott Kupor 發了個標題頗具哲學性帖子,題為《什麼時候 “Mark” 會不算 Mark?當它是一個風險投資的 Mark 的時候》"(原文:When is a “Mark” Not a Mark? When it's a Venture Capital Mark. Mark 意為 “標誌、標記”,也是公司裡 Mark 的姓名,這個標題一語雙關)。時至今日,該公司仍對該報導將 “標記”(Mark)與 “回報”(Return,華爾街日報的用詞)混為一談保持異議。
我要求 Kupor 為另一篇報導說話,他拒絕了。“現在,我們要堅持我們的推特戰爭(笑臉)。”
我回答說:“直接發佈吧(go direct)。” 然後他又給我發了一個笑臉。
Winkler 報導發布的幾個星期之後,Marc Andreessen 刪除了他的舊推文,然後基本上就從社交網絡上消失了。(我懷疑 Winkler 的報導在事後看來是站得住腳的,但需要有人向我透露他們的回報)。
到 2017 年的時候,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這件事(在我看來)已經鞏固了記者們揪出無良創始人的意圖。
記者和他們的沿海地區讀者無法移除白宮裡的強人,但他們至少可以讓矽谷的領導人擁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再加上記者們在努力複製 Harvey Weinstein 關於 #MeToo 的報導,他們走上了社會急需的、激進的問責之路。
2018 年,Facebook 在《紐約時報》即將報導之前迅速地公佈了有關劍橋分析公司的信息(當時該公司內重要的通信主管成員中包含了 Wennmacher 在 Outcast 時期的聯合創始人 Marooney),這是在負面新聞被報導之前搶占先機的一個重要實例。Facebook 對《紐約時報》的蔑視似乎只是鞏固了媒體的看法——那裡存在一個真實的醜聞,它是另一個科技傳播高管和報導科技行業的記者之間關係惡化的信號。
隨著矽谷和媒體之間的關係走向破裂,a16z 採取了另一種營銷策略。該公司一直在建立自己的媒體業務,於 2014 年聘請了在《連線》雜誌擔任過意見編輯 Sonal Chokshi。Chokshi 擔任該公司的主編,管理著一個不斷擴大的流行播客 “艦隊”。
今天,a16z 的 200 名成員中大約有 10% 的人在其營銷團隊工作,且該公司正在擴張其編輯業務。
該公司周圍的人都知道 Chokshi 的內部媒體戰略是公司的未來。一位通訊人員告訴記者說:“他們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家媒體公司。”
長期以來,許多公司和風險投資公司都在嘗試內容營銷——Medium 上那些帖子就是發揮著這方面的作用。Wennmachers 和 Chokshi 的運作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做得很好,規模更大。他們的播客實際上是很有趣的。由於媒體對科技行業採取了極其消極的姿態,人們對更加樂觀的報導就會有更大的需求,而 a16z 就可以滿足這個市場需求。
與此同時,該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了與媒體的合作。我與一些頂級媒體的記者談過這一點,這就是大家的共識。該公司在過去的幾年一直很安靜,甚至銷聲匿跡了。a16z 大多時候都不參與媒體報導,只為《福布斯》的 “Midas 名單” 寫過一篇報導——它是當今科技行業中最無恥的正面媒體來源之一。
Andreessen 已經開始在公司的投資組合公司 Clubhouse 的聊天中插話。他的評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該公司的沉默有多少是戰術性的?又有多少沉默只是反映了已經滲透到該公司領導人的反媒體精神?
我在 Substack 這樣一個 “直接發布” 的平台上發布這份報導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它屬於 a16z 投資組合裡的公司。
在最近一次的感恩節期間,加密貨幣公司 Coinbase 發表了一篇博客文章,文中對即將到來的重要新聞報導發出了警告。Coinbase 本質上是圍繞著風險投資公司 a16z 旋轉的一顆衛星,該公司負責溝通的副總裁是 Milosevich,他是 Andreessen 長期以來的公關處理者,曾處理過 Conrad 下台的報導。
該公告中寫道:“《紐約時報》正計劃發表關於 Coinbase 的負面報導。”Coinbase 是搶在新聞報導之前發布了博客文章,在科技媒體和他們所報導的公司的微妙的雙人舞之中,這無疑是一個大膽且有意為之的動作。這個動作是由幕後的通訊專家促成的。Coinbase 的帖子裡還說了一句:“我們不在乎《紐約時報》怎麼想。”
這是一句令人瞠目結舌的話,Milosevich 多年來一直在幫助 a16z 討好媒體,並在多份雜誌上對 Coinbase 董事會成員 Marc Andreessen 進行過介紹。
在報紙還沒有發表調查報告的時候,堅決支持者們就選擇了自己的立場。《紐約時報》記者 Mike Isaac(推特頭像是 Charmin bear)在推特上寫道:“這種搶先一步的企圖讓人心驚膽戰。它固定了即將發布的報導的讀者群體,並毀掉了他們(對)媒體的所有信任、聯繫。”
“直接報導教會”(the church of going direct,此處是一種戲稱)的首席使徒 Balaji Srinivasan 轉發了他的推文並回复:“誰會相信紐約時報? ”
那一周的星期五,《紐約時報》刊登了標題為《代幣化門面主義化:黑人工作者在加密貨幣創業之王的鬥爭內幕》(Tokenized': Inside Black Workers' Struggles at the King of Crypto Start-Ups)的報導,文中提到 “23 名現任及前任 Coinbase 員工(其中 5 人實名發言)的發言以及內部文件和對話錄音表明,Coinbase 這家初創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在為管理黑人員工而感到吃力。”
但報導刊登後,a16z 卻像什麼都沒發生,後於 12 月出版了一個精心製作的圖文並茂的系列報導,取名為《社交反擊》(Social Strikes Back)。它看起來就像你能在《財富》或《連線》上看到的文章,但裡面當然沒有用專門的篇幅來探討該公司對 Coinbase 的企業文化應承擔的罪責。
Adam Mendelsohn(負責 TPG 的傳播事務,LeBron James 的長期媒體顧問)表示:“科技公司必須問問自己,他們是否能致力於發揮媒體在知情社會中的作用。自行發布消息並不難,但自行發布並一定能使你發布的信息具有正確性。”
很少有人能像 Wennmachers 那樣了解媒體,但她也看到了媒體黑暗的一面。
在科技媒體想要塑造烏托邦式的神話的時候,Wennmachers 見識過他們有多麼渴望地接到她的電話。現在媒體對科技公司的態度轉變了,她塑造媒體的品牌也就不那麼有力了。現在,記者們被困在她不喜歡的敘事當中,她自然會得出「自己反正也不需要記者了」的結論。
她的想法很有可能是對的,不與媒體合作對 a16z 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策略。該公司擁有直接與受眾對話的工具。但她的這套策略對全世界有好處嗎?與獨立媒體接觸難道就沒有價值了嗎?
為了撰寫這篇報導,我在保證不引用她發言的條件下與 Wennmachers 本人交談了一個多小時。Wennmachers 讓我寫清楚,她堅決不同意這篇報導中的許多特徵和事實。
很遺憾,我無法透露她在交談中的其他言論。
*深潮 TechFlow 是由志願者和實習生驅動的深度 Blockchain 內容平台,致力於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有態度的思考。
免責聲明:作為區塊鏈信息平台,本站所發布文章僅代表作者及嘉賓個人觀點,與 Web3Caff 立場無關。本文內容僅用於信息分享,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及要約,並請您遵守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相關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