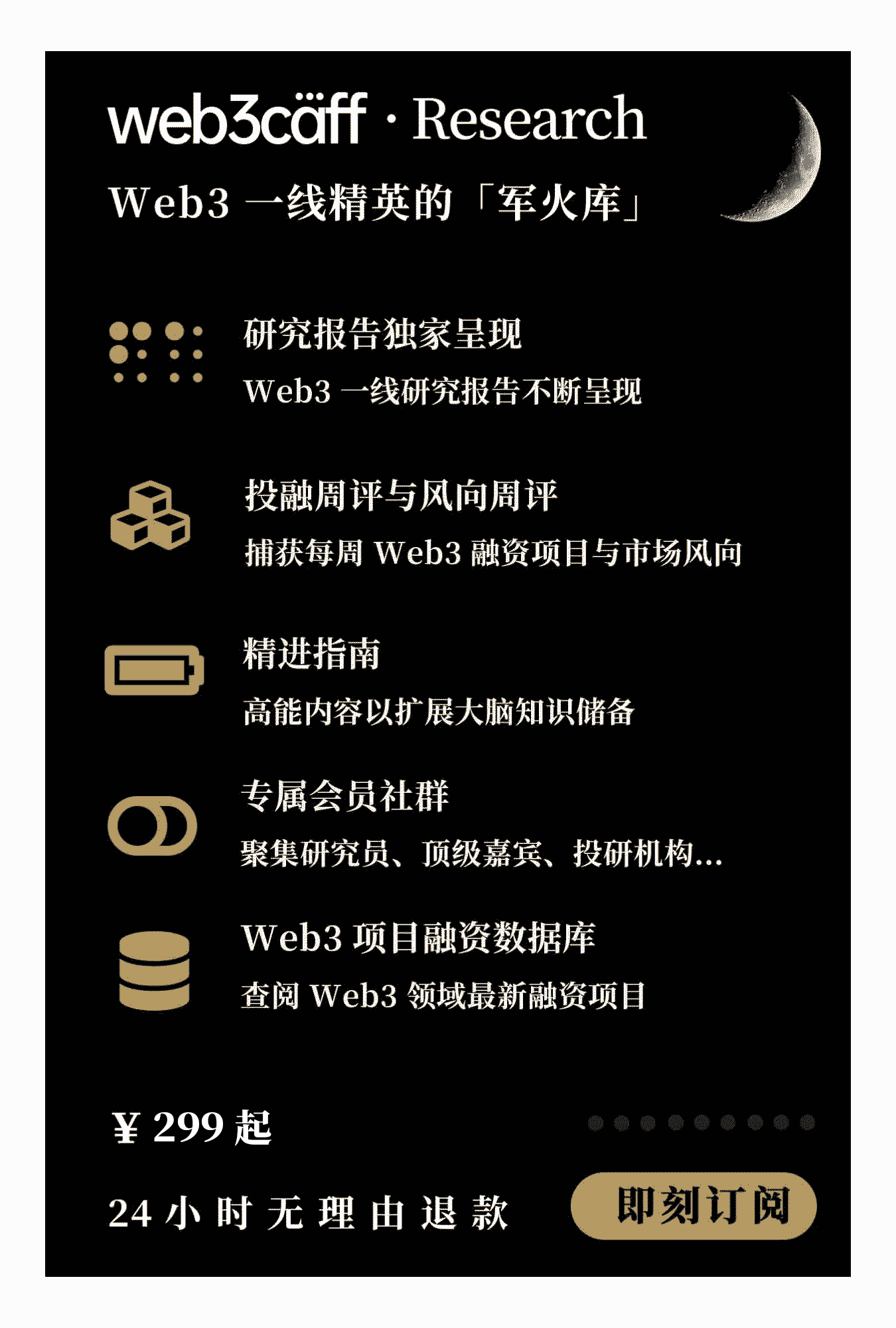通過積極的對話,與文明共同進化。
作者:馮光能,歪脖三觀簽約作者,小光的修真世界創始人
編輯:卡卡
封面:Photo by Julien Moreau on Unsplash
圍繞在一個天才身邊的,是一「城市」有趣的人。 在過去,城市作為人的聚居地,孕育了豐富多元的整體人格,個體人格在整體人格當中得到浸潤和發展。 如今,工業文明的現代城市變得日益複雜,專業化的人變得日益單一,這就需要我們反思工業文明的基本邏輯,從歷史中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為了回應文明面對的諸多挑戰,我們需要對話,積極擁抱現代技術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可能性,用理想的數位城邦照亮工業城市的革新道路,把「城市」的進化和觀念的進化、技術的進化、規則的進化、肉身的進化看作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 數字遊民有希望作為文明的節點,通過積極的對話,與文明共同進化。 -歪脖三觀
前不久,SeeDAO 贊助者唐晗在 《技術奇點與組織挑戰》中提出了「時代駭客」的概念,認為在我們這個系統性危機日益嚴重的時代,如果有人能夠全域地反思整個時代,甚至把整個時代先黑掉,那將會是一件非常有詩意的事情。
在我看來,這其實就是在呼喚 Web3 時代的達·芬奇。 在文藝復興時期,作為全才,達·芬奇思考的許多問題都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 這件事情會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挑戰。 比如,假設我以後準備要一個 AI 小孩,我可以創造一座怎樣的「城市」,就有可能讓它的生活變得像達·芬奇那樣豐富而有趣呢?
達·芬奇的成長環境
聽過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 《直上雲霄》展覽講解的人都知道,達·芬奇不僅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同時也是一位科學家、工程師、發明家,更厲害的地方在於,達·芬奇對問題的思考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人。 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全才。 那麼,達·芬奇為何能夠成為一個全才呢? 為什麼達·芬奇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而沒有出現在中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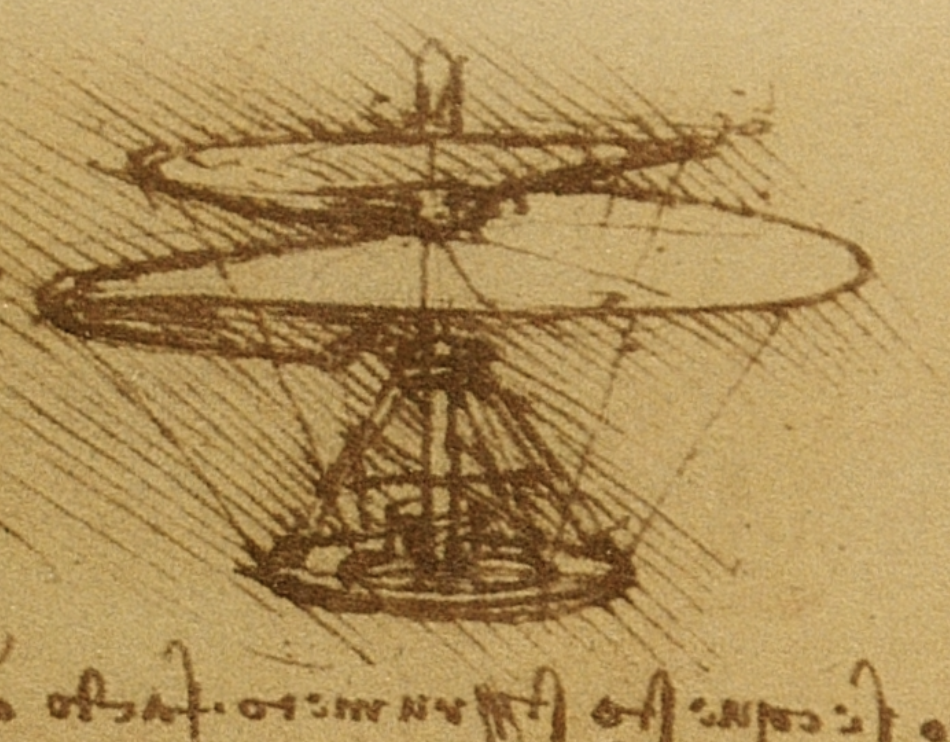
對於第一個問題,大家有過許多觀點,有人認為和達·芬奇童年的鄉村生活有關,有人認為和達·芬奇在韋羅基奧的工坊學習經歷有關,有人認為和一位遠方的導師阿爾貝蒂有關,有人認為和達·芬奇喜歡使用速記法有關,有人認為和達·芬奇喜歡用左手寫字有關,有人認為和達·芬奇旺盛的好奇心有關...... 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對於第二個問題,大家可能會感到很可笑,這個問題就好像是在問:為什麼李白、杜甫出現在中國,而沒有出現在中世紀歐洲呢? 事實上,每一個天才都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根植於他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文明的歷史積澱是存在巨大差異的。
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追問達·芬奇如何變得卓越,不妨著眼於他的成長經歷和成長環境。 在這裡,艾薩克森的 《達·芬奇傳》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一方面,達·芬奇一生都對世界懷有強烈的好奇心,能夠提出視角非常獨特的的問題。 比如,當觀察啄木鳥像打樁機一樣敲擊樹木時,達·芬奇會思考,啄木鳥的舌頭長什麼樣? 看見水裡魚兒靈巧地轉向,達·芬奇會思考,為什麼魚的轉向比鳥要容易,水明明比空氣要黏稠啊! 當觀察豬的肺部時,達·芬奇會思考,如果給它充氣,它到底是長和寬都增大,還是只有寬度增加?
另一方面,在我看來也更為重要,就是達·芬奇生活過的城市都很偉大,他本人也對城市充滿了熱愛。
我們都知道,1482 年的時候,30 歲的達·芬奇感到佛羅倫薩太卷了,就搬到了米蘭,並且很快認識了新的好朋友。 在米蘭期間,達·芬奇非常關心城市的發展,關心米蘭城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環境,會主動思考「如何測繪米蘭城和郊區」、“如何繪製米蘭城地圖” 這樣的問題。 同時,米蘭城生活了非常多優秀的人,達·芬奇能夠和他們對話,比如,當思考 “如何由三角形求得同等面積的正方形” 時,達·芬奇能夠向算術老師請教; 當思考「費拉拉塔牆壁的構造」時,達·芬奇能夠向炮兵軍士吉安尼諾請教; 當好奇「在佛蘭德斯冰上行走是怎麼回事兒」時,達·芬奇能夠向本尼德托·波蒂納里請教; 當思考「如何用倫巴第人的方式修理船閘、運河和磨坊」時,達·芬奇能夠向水力學老師請教; 當思考 “太陽的測量方式” 時,達·芬奇能夠向法國人喬瓦尼請教...... 在一天當中,達·芬奇就可能找數十個人請教自己感興趣的問題。
試想,如果我們每天都能夠自由地提出數十個問題,並且與擁有相關知識的人對話,那麼一年、兩年,或者十年之後,我們難道不會擁有無比開闊的視野嗎?
從技術環境來看,我們現在擁有互聯網,在某種意義上,對話比達·芬奇那個時代更加方便快捷了。 而且,互聯網有許多資源,如果我們擅長搜索,我們能夠獲取的信息的品質未必就比達·芬奇要低。 但另一方面,我們大多數人反而沉淪在資訊繭房當中,每天都被各種平臺根據演算法推送各種資訊,還有一些年輕人變得不願意和人打交道,寧願一個人玩手機。 除此之外,由於生活中有太多無主之債等著我們回應,我們往往缺少閒暇,我們的好奇心與達·芬奇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尚未擁抱我們所處的技術環境,沒有積極擁抱技術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可能性。
兩種經濟迴圈模式
為什麼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達·芬奇這樣的全才? 我們不妨從經濟循環的視角切入。
伴隨技術環境的發展,現代工業文明呈現出「器殺道隱」的特徵,就是說,技術變得越來越體系化,人卻變得越來越專業化。 人為了適應整個技術體系,為了維持技術體系的運作,為了在技術體系中佔據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態位,往往會選擇在某個非常小的領域紮根,從而讓有限的自我與龐大的技術體系耦合,以便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技術體系所規定的目標。 於是,人逐漸習慣於聚焦手上的事情和現成的目標,習慣於按照操作性思維生活,逐漸失去了談事情的能力,逐漸遺忘了道的存在。 由於世界太過複雜,而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們感到自己無法再成為像達·芬奇那樣的全才,也感到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成為像達·芬奇那樣的全才。
不知不覺,我們育人的理想也被工業文明的邏輯預先規定了,也就是培養專業化的人。 如果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圍繞育人這個方面,文藝復興時期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經濟迴圈模式存在根本性的區別。
事實上,文藝復興時期擁有卓越才華的人往往並不算富裕,依賴資助,就像我們今天也有許多貧困大學生資助一樣。 區別在於,資助的形式和目標不同。 比如,當時佛羅倫薩資助達·芬奇的美第奇家族也資助了波提切利、米開朗琪羅、費奇諾等人,讓他們在工程、繪畫、雕塑、哲學等領域自由地思考和創造,也讓家族的子弟與他們交往,共同成長。
比如波提切利也像達·芬奇一樣熱衷於繪畫,美第奇家族就向他提供資金,用來維護工作室和購買昂貴的繪畫材料,委託波提切利創作,並創造合適的社交環境,從資金、場地、材料、社交、平臺、氛圍等多個方面激發波提切利的創作熱情和創作靈感,同時對波提切利的作品進行推廣和宣傳。 由於波提切利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援,所以完成了一幅又一幅不朽的作品,《維納斯的誕生》就是其中的一幅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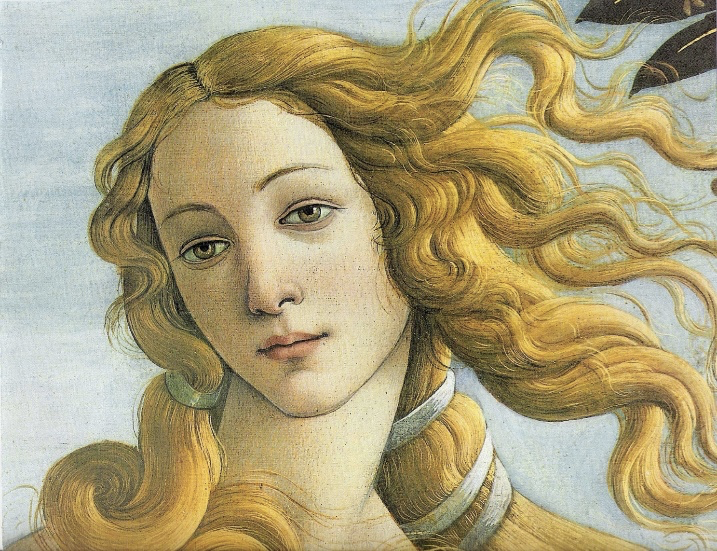
在美第奇家族的資助下,像波提切利、米開朗琪羅、費奇諾等卓越的人不需要關心生存問題,可以把所有精力都用來創造,進而讓佛羅倫薩這座城市變得更加光輝和美好。 可以發現,對於美第奇家族來說,佛羅倫薩的城市發展、家族的經濟迴圈、對卓越人物的支援、對社會秩序的維護都屬於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資助的方式主要是提供平臺,讓被資助者自由發展,而沒有預設目標。 同樣,誰能得到資助,也沒有固定的標準,更多是憑藉在公共領域展示自己的作品和才華,依賴逐漸樹立起來的名聲。 而對於美第奇家族來說,通過這種支援得到的回報是多個方面的,不僅僅是名聲,也包括傑出的作品、美好的公共生活、有生機的人際關係。
而到了現代,資助的條件與目標都同樣被工業文明自身的邏輯預先規定了,一些有天賦的人即便獲得了資助,也必須讓自己變得專業化,朝向一個預先規定好的人設發展。 這個人設需要能夠在工業文明當中扮演好一個角色,從而為出資者帶來效益。 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以人為本的經濟迴圈模式轉化成為了工業文明以錢為本的經濟迴圈模式,人成為了大工業體系發展過程中的附庸。
之所以如此,與無限貨幣的觀念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不能忽視「資本增殖」這一觀念的歷史性沉澱:在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貨幣成為了沒有上限的數字,競相追逐資本的增殖就成了人類活動的常態。 由於貨幣是沒有上限的,所以有錢人總是可以想辦法掙更多的錢,這樣掙錢就成為了無休無止的活動。
我們需要意識到,在現代工業文明當中,被工業邏輯支配的並不只是普通人,也包括諸多資本家。 由於金融活動成為了專業化的活動,所以資本家考慮問題的方式更多也是專業化的,他們也不能擺脫對現代金融活動的路徑依賴。 這也就是說,他們思考的問題有時仍然是如何創立專案賺取更多的錢,從而更好地在工業文明中消費,而不是思考如何用這些錢來改善社會,改善文明,或者改善自己身邊的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掙錢的目的總是指向掙更多的錢,而醫患矛盾、環境污染、社會結構僵化、貧富分化、階層矛盾加劇等問題,並不在金融領域的關切範圍之內。
這都是正常的,問題不僅僅出在資本家,也是出在每一個對工業文明缺乏反思的人身上。 之所以這樣,主要也是由於世界的工業化已經持續幾百年了,而現代人都太過年輕。 工業化時間長意味著,工業文明的邏輯已經沉澱在了現代技術環境的每個角落,形塑了每個現代人的成長歷程。 現代人太過年輕意味著,我們最近一百年出生的人,都生活在工業化的進程當中,無論老人還是年輕人,大家都習慣了圍繞效率和掙錢談事情,也就習慣性地把這套語言看作唯一用來談論事情的語言,進而逐漸對那些和掙錢無關的話題感到排斥。
於是,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我們試圖脫離掙錢談論理想,或者稍微對現實加以批判,不出三句話,就會招來質問:你不掙錢如何生存? 你生存都做不好,憑什麼談論理想? 你連眼前的小事情都沒做好,憑什麼說自己要幹大事? 於是,「反思工業文明,探尋新的秩序」這件與每個現代人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事情反而幾乎不可能在公共生活中得到談論,似乎不談論這件事情文明就能永遠向好發展一般。
工業文明中的兩種對話
就目前來說,工業文明構成了我們進化的起點,現代世界的工業化已經持續了接近三百年,我們最近一百年出生的人都生活在工業文明當中,也就不得不在接受工業文明賦予我們的實際性的條件之下,找尋新的希望,一步一步走出新的道路。
工業文明的基本矛盾是「器殺道隱」。,也就是技術的體系化與個人的專業化。 這是由於我們對工業文明自身的邏輯缺少反思的緣故。 而無論從整體反思工業文明,還是探討新的秩序,需要的都不是一張現成的藍圖,而是持續的對話。
在持續的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帶出了彼此對世界的解釋,這種解釋中的真理性在遺忘的過程中得到沉澱,不斷更新我們對自己 “如何作為” 和 “成為誰” 的理解,這種理解影響了我們的行動策略,任何行動都是從某種解釋出發並且試圖回應某種寬泛預期的行動。 只有當我們在對話過程中對工業文明的反思越來越清晰,對接下來要做的事情越來越有想法,我們才能逐漸擺脫工業文明對我們的支配。
在我們這個時代,嚴肅的哲學、歷史文本與公眾的對話變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同時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 原因在於,公眾的內心對哲學與歷史是持有一種迴避態度的,或是表現為敬而遠之,或是表現為嗤之以鼻; 而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學者,也被各種評價標準裹挾,忙於閱讀、寫作和發表論文,甚至連靜下心來寫一本專著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提如何與公眾進行持續而深入的對話了。 除此之外,在海德格爾所謂的集置的促逼下,公眾對對話本身也有一種排斥的心態,有時會著急地發問:你說了這麼多,有什麼用呢? 你倒是說怎麼做啊!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 我們不能把馬克思的話理解為改造世界比解釋世界重要,原因在於,改造世界的前提依然是解釋世界,我們如何改造世界,取決於我們如何解釋世界。 而且,就像海德格爾所說,任何對世界的解釋都是一種對世界的改變。 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關於改造世界的片面認識正在遮蔽和阻礙我們對世界的解釋,這種遮蔽和阻礙並不是取消了對世界的解釋,而是把工業文明對世界的解釋默認成為了唯一的解釋。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馬克思之前的哲學家,還是馬克思之後的哲學家,他們的真正問題其實不是對世界的解釋不夠好,而是沒有讓自己對世界的解釋與更多的公眾產生對話。
為此,我們可以區分「獨善其身」的對話和「兼濟天下」的對話。 所謂「窮」,並不是說沒有錢,而是說思想鎖閉、缺少志向與抱負的狀態,這種狀態下的人無力關心文明的整體境遇,安頓好自己是第一位的; 所謂「達」,說的就是一個人視野開拓、有能力持續地反思整個文明,這種狀態下就可以嘗試開始說事和做事,在言說和行動的過程中持續反思文明,逐漸贏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和支援。
這兩種對話狀態與個人貧富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它們的區分仍然首先是哲學層面的,前者把個人的境遇置於優先考慮的位置,後者把文明的境遇置於優先考慮的位置。 許多人喜歡用極限狀態說事情,常用的論證是,個人生存都顧不上了,如何關心文明,或者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 實際情況是,現在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其實不存在問題,只是由於大家都優先考慮自己,所以帶來了既無止境也無止盡的內卷,造成了不必要的內耗以及社會的持續惡化。 反過來,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從文明的境遇出發考慮問題,不斷完善自己,照亮身邊的人,社會的改良才是有希望的,所謂是「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
一些折中主義者喜歡說關注細節與關注大事不矛盾,把細節做好了才能成事,做大事依然不能忘了關注細節。 這是一種自大的表現,這種說辭根本沒有意識到,有限的人在反思文明整體時,究竟需要克服怎樣的困難,需要靜下心來地閱讀多少書本,需要進行多少次反思和自我懷疑,需要如何一次次錘鍊自己的思想,需要迎接多少次來自普通人的不明就里的質疑。 理想主義者的道路是漫長的,一件大事所蘊含的可能性或許需要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對話才能真正展開,言說這件大事的歷程,其實就是文明秩序的發展歷程。
工業文明對人提出的要求其實就是專業化,消費社會中的各個崗位其實並不需要個人有什麼創造力,也不需要有廣博的知識,僅僅需要個人能夠按部就班地完成既定任務。 所以,只要人具備一些基本知識,稍加培訓能夠上崗,上崗之後能夠儘快熟悉業務流程,就算滿足了工業文明的育人需要。
這也就是說,專業教育是體系化的,帶來的是關於如何獨善其身的對話——雖然從事專業工作的人也對社會產生貢獻,並且這些貢獻是實質性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從事專業工作的人無法反思和改良工業文明的整個秩序,無法回應形如社會結構僵化、學術工業化、金融泡沫、虛無主義、戰爭、人口老齡化、氣候變暖、能源危機、物種多樣性降低等日益嚴重的問題。 他們所做的事情其實是與大工業體系耦合:對於專業化人才來說,需要關注的問題是操作流程的合規定性而非所做事情的目的與意義,因為每個工作的形式都已經先行給定了,而這些工作的目的都指向了維持大工業體系的運轉。 簡而言之,專業教育的目標是明確的,效率是可以評估的,其價值也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
毫無疑問,專業教育並不能孕育出達·芬奇那樣的全才,也不可能孕育出「時代駭客」。。 如果我們要探索文明的未來,仍然試圖在大工業時代的洶湧浪潮當中找尋到新的希望,我們就需要把更多的視線聚焦到 “兼濟天下” 的對話當中,這也就關涉到我們常說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和啟發教育。
通識教育關注知識的統一性,博雅教育關注人格的統一性,啟發教育關注真理的顯現。
對知識的關注和自身人格的發展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 比如,按照柏拉圖的說法,高貴的知識具有啟迪靈魂的功效,“當某人的慾望流向知識和一切類似的領域,我想,它們就會湧向只屬於靈魂本身的那種快樂,把軀體所能感受到的種種快樂拋在後面,如果這人並非表面是而是真正是一個愛好智慧的人。 ”
真理的顯現不是對天穹之上的理念世界的揭示,而是把每個人意見中潛在的真理「引發」出來,在公共領域當中得到大家的見證。 這正是「蘇格拉底的助產術(maieutic)」:在雅典廣場(Agora)上,蘇格拉底的言說活動總是以問題開場,原因在於,在言說之前,蘇格拉底並不知道他人擁有什麼可言說之物,不知道他人的世界結構,他只能以提問的方式引出他人的世界顯現,引出每個人的意見中所固有的真理。 這也就是說,雖然對同一個問題,每個人都會持有不同的意見,但意見中的真理性可以在公共領域中的對話當中如其所是地展開。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對話是展現真理的一種方式,那麼即便脫離了蘇格拉底的助產術,我們也能在對話過程中相互啟發。
也就是說,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和啟發教育並不能從體系化的角度來認識,它們決不是三種不同的教育體系,它們永遠不能被體系化,它們永遠保持開放; 它們可以但不一定是教師對學生的點撥和解惑,它們的本質其實是在每一次真誠對話中都可以蘊含的三個維度。
如果我們把視線放到工業文明的學科分類當中,關於歷史、哲學、藝術、文學、科學的教育似乎和 “兼濟天下” 的對話更加相關。 但事實上這之間也沒有必然關係,因為工業文明的學科分類和一系列量化評價體系已經緊密綁定,而與個人心智的健全、對事物的感受力、對萬物一體性的領悟不存在必然關聯。 比如,一個發表了多篇論文的哲學博士生可能堅守初心,仍然是一個真正愛智慧的人,也可能沒有掙脫工業文明的諸多要求,淪為了一個學術工匠。
與「兼濟天下」的對話緊密相關的,其實是「城市」的形態與秩序。
“城市” 與對話
按照芒福德的觀點,對話是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 這種觀點有著深厚的邏輯必然性。
人與人的聚居並不是一種空間層面的靠近,而是在共同的故事中存在,使得同一座城市的人成為共同體的,不是城牆,而是關於城市的故事。 比如,旅居在 A 城的遊客由於背負著 B 城的故事,所以雖然遊客的肉身在 A 城中,遊客的吃喝拉撒睡在 A 城中,但他卻不屬於 A 城共同體,除非遊客被 A 城的故事同化,成為了 A 城的居民; 或者遊客 A 接納了一個新的故事,這個故事在保留 A 城與 B 城的獨特性的同時,消解了 A 城和 B 城在概念上的對立,從根本上杜絕了 A 城與 B 城進行對抗和戰爭、甚至結盟與合作的可能,而是讓 A 城與 B 城的居民通過彼此的差異性來認識到自身的獨特性。
事實上,上述狀態是一個永遠無法企及、永遠可以不斷趨近的理想狀態。 原因在於,城市的故事從不會一勞永逸地講完,而是在一次次對話中展開,每個人的存在方式都在一次次對話當中改變,並在一次次對話當中沉澱。 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阿倫特所說的有限的人才能通過源源不斷的美言嘉行在公共領域中尋得不朽。
對話總是依賴媒介和我們在媒介世界中的共在。 即便是面對面的對話,也不僅僅依賴空氣傳遞聲音的振動,也不僅僅包含了我們對手勢、表情、情緒和態度的識別,更是由於我們首先已經共同在場了,由於我們已經在世界的大舞臺上登場並且作為有待彰顯自身真理性的人而相遇了。 古希臘的廣場之所以會成為世世代代學者心目中不可磨滅的記憶,就在於廣場作為公共領域,把眾人邀請到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以及諸神的注視當中。 廣場上的每個人,都是組建共在領域的一員,大家共同存在於同一個領域當中,每個人的個性都會聚、沉澱,凝聚為共同體的整體人格。
而伴隨技術環境的發展,我們的共在領域的存在方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乘坐地鐵。 站在地鐵上,就彷彿是站在一個巨大的滑板上,按道理來說,這有希望成為一個比古希臘廣場要酷炫得多的共在領域:地鐵在飛馳,每個人在通往不同的目的地的旅途中相遇並會聚,大家擁有自由敞開地對話的可能性。 但事實情況往往並非如此。 在地鐵上,更常見的情形是:每個人都拿著手機,通過手機進入到互聯網世界當中,保持安靜,從而避免影響他人。 在這個意義上,互聯網已經成為了比物質世界更加真實的公共生活空間。
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原因並不僅僅是像胡翌霖經常說的,由於大多數人在現實中過得不如意,於是通過互聯網來躲避現實。 如果我們認可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是對話這一前提,那麼互聯網顯然比物質世界更加有利於對話,而且幾乎是全方位的超拔:
(1)互聯網的對話更加便捷,能夠跨越空間與時間。
(2)互聯網能夠保存對話,人們所言說的內容可以通過文字、視頻、音訊等方式保存下來。
(3)互聯網能夠把「凝縮」和「展開」活動外在化,也就提供了更自由的選擇可能性,面對一個超連結,如果感興趣,我們可以選擇點開,如果不感興趣,我們也可以不點開,而面對面交流時,如果眼前的人滔滔不絕地言說,我們則會感到苦惱。
(4)互聯網同樣可以支持即時的多方會談,比如通過各種會議軟體。
(5)互聯網不要求即時回應,大家在對話過程中有更多的緩衝時間。
(6)互聯網可以支持多種形式組合的對話,比如發送一封郵件,可以附帶文檔、圖片、視頻、超連結等資訊,讓言說者的意圖得到更加充分的表達。
(7)互聯網可以更容易支援想法共創,比如通過 notion、各種在線文檔。
這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互聯網中的「城市」要比線下的城市更加切近於城市的起源。 目前而言,數位城市的發展其實才剛剛開始,不過已經可以發現其中所蘊含的巨大潛能。
比如,麵包樹花園的 Jenny 成立了一個愛智慧成長營,會定期組織線上和線下的共讀、共學、共話、共遊活動。 雖然我與 Jenny 相隔很遠,不過通過互聯網,也能參與到他們的線上活動當中。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了許多有趣的朋友,接觸到了鮮活的思想。 比如,在李達看來,國學就像太極拳,理工科就像六脈神劍,藝術就像乾坤大挪移,每一樣學科都可以看作是一門武功,而共創交流會就像華山論劍,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施展自己的哲學,把那些自己傾注了生命的領悟與他人分享。 比如,在 Ivan 看來,閱讀哲學書籍時可以圍繞文本,一段一段地分析,閱讀歷史書籍時可以圍繞問題,大家讀不同的書,分享、對話,回應同一個問題。
在這樣的交流會當中,地理的距離並不能構成阻礙,由於大家都真誠地分享,所以能夠通過語言,共用彼此的記憶。
如果說愛智慧成長營讓我感到親切,那麼 SeeDAO 的數位城邦作為一個宏大願景則是讓人感到震撼和嚮往。
目前,SeeDAO 已經構建了一張全球的網路,線下的城市聯絡人已經遍佈全球的 10 個城市,比如矽谷、紐約、新加坡、迪拜、香港、北京、上海...... 在 SeeDAO 贊助者白魚看來,DAO 真正要探索的其實是一個公共領域,一個為全世界人提供公共生活的線上空間,他們要做的事情是發展這個空間,維護這個空間的存在,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這個空間建立更豐富的聯繫,讓每個人都感覺自己與這個空間相關,讓大家能夠在 DAO 中進行自由地創造。
雖然 SeeDAO 的數位城邦還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比如數據不夠完善,人員流動頻繁,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但同時,我們也能發現,在這個大浪淘沙的過程中,許多喜歡靜下心來做事情的人,在 SeeDAO 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屬感,他們的成長與數位城邦的建設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
按照另一位贊助者唐晗的說法,雖然 SeeDAO 會按照 PoW 原則根據社區成員的貢獻來發放 Token,不過就目前來說,SeeDAO 的發展歷程更像是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 許多金融投機分子來了又離開,剩下的都是對社區高度沉浸並且能夠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以數位合作社的形式構建 DAO,建立城邦,建立治理、教育、身份、聲譽等各方面的公共物品,而不是直接從資本構建權力。
當然,線上的無形「城市」與線下的城市並不是對立關係,事實上,線上「城市」的發展往往讓線下城市更加具有生命力,比如 706 城市計畫。 目前,706 已經擁有了成熟的線上組織形式和宣傳方式,舉辦了大量的線下活動,這些線下活動都以非商業化的形式展開,實現了價值的非貨幣性交換。 我最近參加了成都 706 假唱組織的「觀系遊戲」,參與者可以選擇一張故事卡牌,結合自己的經歷與思考,對這張卡牌進行闡發,然後邀請金牌主播、哲學家、藝術家、天使、魔鬼等角色給自己提問。 這些卡牌道具就給我們搭建好了一個對話平臺,用不同的方式促使對話的發生和延續,讓每個人都能在講述和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彰顯出自己的獨特性。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了具備文學氣質、妙語連珠、喜歡反思的元音,熱愛科幻小說、熱忱追尋新的可能性的土撥鼠,對教育有著熾熱理想的青夢,正在為家庭和孩子奔波操勞、一門心思想要努力掙錢的朱哥靚,正在實踐自己的理想咖啡館、具有深厚理工科功底的馬文,喜歡做飯、感到生活喪失秩序的托克,喜歡街舞、非常依賴他人、容易陷入焦慮的彥麟, 非常擅長共情的蔚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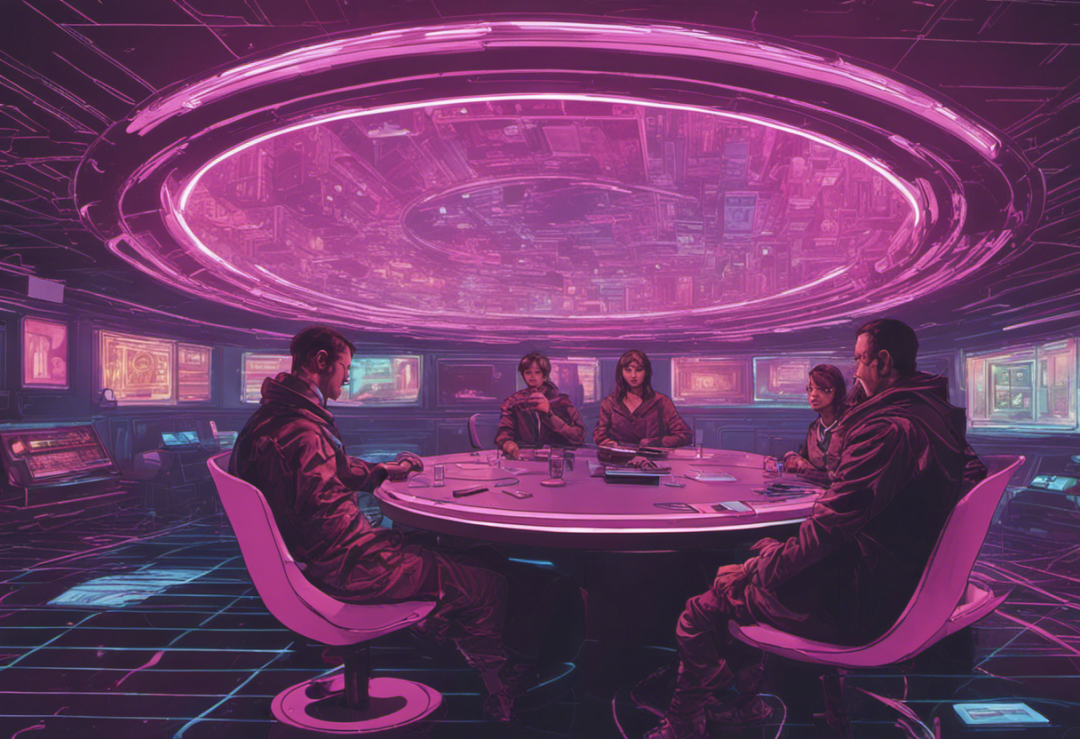
由於脫離了貨幣的約束,大家的交流變得更加輕鬆、自然,更加容易聚焦於他人的訴求,在對話的過程中耐心傾聽、相互啟發,產生共在感與歸屬感。
數位遊民作為文明節點
在我的數位遊民實踐經歷中,我最深刻的感觸其實並不是互聯網給對話帶來的便捷性,真正觸動我的地方,其實是對話的無功利性,類似於 706 所提倡的價值的非貨幣性交換。
在功利性的對話中,由於大家一切都向「錢」看,所以語言不可避免地淪為工具,對話時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確認等級秩序。 這就使得大家關於競爭、博弈、拉踩、順從、忍耐的意向性被啟動,對話的內容也被工業文明的盈利邏輯鎖死了,這種對話是非本真的,甚至會異化我們的言說能力,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變得不願意說話,變得沉默。
而在非功利性的對話當中,對話的氛圍變得更加融洽,或許大家最開始還有所戒備,但是伴隨氣氛的醞釀,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一種召喚,一種存在的呼聲,一種真誠回應他人的意願,感覺到自己和他人都共同隸屬於一個整體,於是言說活動變得敞開,大家在傾聽他人意見的同時也在敏銳地識別他人意見中的真理性與妄念,有時甚至識別到自己的妄念,在覺察到這些之後, 無需有太多準備和籌劃,自然而然地言說,就回應了集體營造出來的語言場。 浸泡在這種語言場中,感覺思想能夠得到自由的生長,身邊的人都是寬容、友善的,時不時就會有啟迪的火花閃現,感覺身心都得到了療癒。

可以發現,在互聯網的説明下,其實我們都有可能像達·芬奇一樣,積極與他人對話,結交更多的朋友,大家相互切磋、共同成長。
誠然,數字遊民的道路並不容易,我認識的一些朋友,比如罐頭,由於堅持非盈利的運作模式,有時候為了經營自己所負責的空房子,不得不帶著家屬一起打工掙錢,在別人籌劃活動的時候,他們提前一個多小時到空房子打掃衛生、準備茶水,然後在活動開始前離開,許多參加活動的人可能都不會見到他們。
不過也正因如此,數字遊民的道路可以非常精彩。 畢竟,工業文明的發展已經趨於極限,人類文明的轉型是大勢所趨。 在這樣的趨勢下,對話將變得更加重要,事實上,對話向來就是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 而數位遊民的生活方式又決定了,數字遊民有更多與他人進行對話的機會,每個數位遊民,都會在生活中結交大量的朋友。
當然,思想的解放仍然是最重要的。 所謂數位「遊」民,其實未必需要肉身旅遊,因為網路上已經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社區,一座座數位城邦正在 Web3 的世界中緩慢崛起,很多時候,數位遊民只需要坐在家裡,就能遨遊三千大世界,正所謂 “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
無論如何,我們確實身處在技術奇點當中,就像袁園所說,奇點並不是一個時間節點,不是一個遙遠的未來時刻,而是一個已經開始的進程。
就目前來看,數位城市的進化正在為數位遊民提供新的生活可能性,數位遊民的活動作為一種案例啟發著城市居民的思想,促使城市居民向數位居民轉型,許多事情都在潛移默化地變化著,新的秩序正在逐漸孕育。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們對工業文明的邏輯有了反思,變得更加朝向他人和世界敞開,也就能夠經歷更多有趣的對話,成為人格更加健全的人,像達·芬奇一樣全面發展,對時代有更多的反思。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進化和「城市」的進化、觀念的進化、技術的進化、規則的進化確實乃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
我們都可以是世界文明史的新篇章的言說者與書寫者。
我們向來同在。
ABOUT
我們是誰
歪脖三觀是一家以 web3 的方式生產內容的中文媒體,也是一場小隊協作模式的創作者經濟實踐。 我們既堅信 web3 是大勢所趨,又篤定在 web3 的時代內容的內涵不會變——有資訊,有洞見,有審美,有趣味。 web3 所饋贈的去中心化、權力平等、分配公平、規則透明、模式互助等,讓我們有自信可以創造內容價值、經驗價值和觀念價值。
我們誕生於 SeeDAO 的 SIP-79 提案,成員大多來自 SeeDAO 社區,有 crypto 老 OG,學界專家,金融專家,媒體人,上班者,大學生......
“歪脖三观” 有两层寓意,一是 “歪脖三·观”,意为去 “观”web3,去见证、记录、传播 web3 的一切。二是 “歪脖·三观”,“歪脖” 想展现的是既认真思考又幽默诙谐的朋克态度,“三观” 鞭策我们要关注底层观念而不只是浮躁嘈杂的表象。
很高興在這裡遇見你。
免責聲明:作為區塊鏈資訊平臺,本站所發佈文章僅代表作者及嘉賓個人觀點,與 Web3Caff 立場無關。 本文內容僅用於資訊分享,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及要約,並請您遵守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相關法律法規。